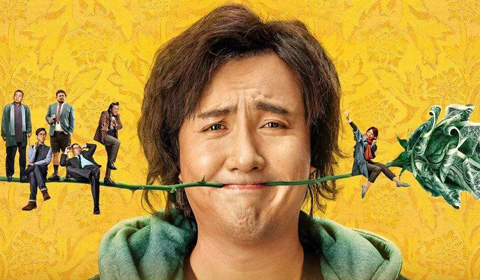有个怪人很温暖
他十几岁参加援越战争,开车。是真正的老司机。因此有次我在他车上,看他边聊天边与别人的车擦着后视镜而过,几乎碰到。心里一惊。再看他,却是笃定擦过去似的。他是个沉稳的人,唯有开车让我觉得漫不经心,颇为有趣。
他父亲读的是圣约翰大学,他说自己读书那几年没怎么正儿八经的学,杂书倒看了不少,市面上的名著,都被翻光了。到今天,他的床头还放着《猎人笔记》,再读《傅雷家书》还是会热泪盈眶,《约翰.克斯里多夫》看了那么多遍还是愿意再读。
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有商人条件罗列清楚的请他做木偶片,觉得可行,于是充满动力的开工。他带领一帮毕业生熬夜战斗,终于做出令自己欣慰的样片。他说,欣慰是因为片子是厂里的年轻人做的,他们刚毕业,那么年轻,能做出这样的东西,我很高兴。
去年国庆前夕年轻徒弟的活儿有问题,未能准时完工,老师心急如焚,却只能等假期归来。
我们说不如加班。他说,节假加班费用是平时的三倍,我们没有钱。
我们说现在随意让员工加班的多老板去了,没事情。
他想了下,说不行,我这里做不到。然后笑了。
他说,现在房子那么贵,大学生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给出的价钱那么低,这是不对的。你们交了那么多钱,读书学习那么久,迈出校园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待遇。
他像许多老师一样叫我们课堂上也讲一点课,但是又说,不要有压力,能讲多少算多少,不想讲就我来讲。他听完我讲的内容,又说,不要准备那么多,一点看法就好了。我知道你们现在面临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准备多了投入精力太大,会搞得很紧张,拿出吃完后一晚上的时间想想,就可以了。
对于论文,他听说我们要做的题目一点不高深,居然说不错,说做自己喜欢的,关注的。也是件好事。
上届学长的论文有一点问题,他说有时一觉醒来,睁开眼就想到他,发愁怎么才能让他保险通关。
他是兼职。每天忙碌的事情很多。课堂见面,我很遗憾,他没有拖堂的习惯。从未有过的,我希望老师能够拖堂。
他年近六十,是国家一级导演。今天上美影辉煌不再,他们唯有做一些别人愿意投资的活儿。他的办公室要跑好几层楼梯,下面的许多房被厂里租出去了,以维持美影厂的运行。
他与别人多次合作,有过激情与默契,也遭遇虚伪与骗局,再与人谈,却始终愿意去相信。
木偶片的样片被商人当自己的成果拿去评奖,拿到很多政府奖金。商人决定自己组个班子拍片,不必与老师合作。然而又担心技术问题,请老师指导下,这样的情况,老师居然答应。他说要发展国产动画,我一己力量有限,既然他们有钱,愿意做,也好。不管是谁做,如果能做好,对于我们国家的动画都是好事,我真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可是老师这样说,我们什么也不能说,唯有自惭形秽。
他说退休后想做点喜欢的事情,从前跟有名的师父学过木模工艺,大概退休能有时间做做了。
据说那个能卖非常好的价钱。可是与老师无关。
前年班上参观上美影,老师给我们每人一张特伟导演的纪念光盘、美影厂邮票;去年放《马兰花》,老师给我们三个学生每人两张电影票;研一没他的课,老师偶尔会请我们吃饭,听我们聊近况,问是否还好;研二上课,教室没开门,老师带着我们去楼下一角咖啡店上课;他热爱动画,却有许多的无奈,只是力所能及的告诉我们所知道的,提供给我们有所帮助的。他说起那些无奈,末了还是以笑结束。他告诉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怀疑的精神,透过表面看本质的态度。有其他院校请他兼职,他却觉得北京遥远,不能真正顾及学生,推了。不管学校是要名义上还是怎样,他只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做事。曾经我有微微的迷茫胡乱说起,他那样认真的找我谈。他的理念很奇怪,似乎做了他的学生,生活情感的困惑也是要负责解决的。
去年的时候我去动画公司工作,被封闭关到郊区的别墅,没能上全课,他没意见,只是告诉我,要注意哪些,怕我吃亏上当。
动画公司做的不开心,之后回来上了一次课,再次看到他那么善意温良的微笑,说着打心底为你考虑的话,突然有了想哭的冲动。
那一刻第一次觉得,不舍毕业。因为我怕毕业后,再看不到这样一张慈祥的笑脸。
这世上恶人好人足够多,博大的人深厚的人肤浅的人虚伪的人足够多,可是如果曾经有那么一张笑脸令你动容过,能忘得了吗?能容忍辜负吗?
是为记。谢谢你。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