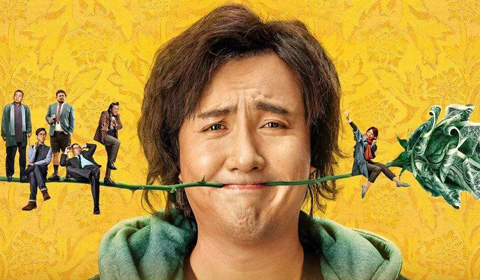你偷过东西吗
我曾经有一帮特别的同学,他们的身份背景迥然相异,年龄跨度从60后到90后。我记得,同桌的年纪刚好和我前面同学的妈妈一样大。大家的经历也五花八门,有人海外十年归来,有人事业小有成就,有人刚刚大学毕业,也有人之前在各处打工。
他坐在我的左前方,话不多,年纪和我相仿,但是已经工作几年,来到班级之前,据说是在社区做保安。
那几个月的学习生涯里,半数同学工作在身,不但经常有人翘课,更有人直到毕业我们都没见过,令大家很替那位同学心疼学费。
而他是每节课必到的。并且,他总是带着相机,将老师在课上放的幻灯片教案一页页拍下来。通常,班级里有谁逃了课,或者是笔记没记全,就会去找他借。
虽然他听课认真,却总是听不懂,有时候我们解释完,他依然一脸迷惑。不过,就算不明白,他依然比谁都听得多,像一个“屡败屡战”的战士。乃至毕业后,大家返乡的返乡,工作的工作,独独是他,每天坐一个多小时公车去学校蹭课。
他与我们交流不多,有次几个朋友一起火锅小聚,大家一通海聊,大声地争论,气氛在涮羊肉的热气腾腾里愈发地热闹。但只有他,从头到尾都在默默做听众,不插嘴也不吃饭。我们半晌才注意到,忙对他说,怎么不吃啊?你吃呀!
他说,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听听你们说话,学习一下。
我们一愣,也不再多说,一面舞动起筷子,一面喊他赶紧吃东西。
他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很久之前的一件小事。
那时候还没毕业,有一次上课,我偷偷写了个故事,一千字的样子。下了课,他转头来聊天,看到我在稿纸上勾勾画画,顺手要了过去读起来。
那是一个美女小偷的故事,女主角身手不凡八面玲珑,虽然远不能与《偷天陷阱》《天下无贼》中的偷天大盗相比,却也游走在“偷盗的世界”里潇潇洒洒。
这个故事只是心血来潮写着玩的东西,写完了随手丢掉就是它的命运,因此也没打算邀请别人提什么意见。
没想到的是,他看完我的故事,脸色渐渐有些异样,终于按捺不住说:“你偷过东西吗?你知道怎么偷东西吗,知道偷东西的心情吗?写得这么轻松,小偷还是个女的,偷起来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偷东西有那么好玩么?!”
他的声音不高,脸上并没有不悦,只是一口气极认真地质疑了一连串,以表示自己对故事虚假情节的反对,语气里透着一股“愤愤不平”。
我很是意外,愣在那里,半晌接着他的话茬小心翼翼道:“难道......你偷过东西啊?”
他头也没怎么抬,依然看着故事,简简单单地回答我:“偷过。”
我又是一愣,轻轻“啊”了一声,不知道这话怎么接,心里却在问:在哪里偷的,危险不危险?
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的尴尬。只是放下故事,说我写的东西“不科学”,然后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偷东西的经历。
那时他刚刚结婚不久,二十出头,带着老婆从遥远的家乡奔赴北京,为了省钱,租了间极便宜的地下室房间。
但是工作却异常难找,那段时间,两个人每天外出求职,出发天还未亮,回家月已西升,而“好消息”却仿若海市蜃楼,始终只是两人眼前互相安慰出来的幻象。
他们失业、穷困,眼看就要吃不上饭。事实上,也真的经历过了没钱吃饭的窘境。
那天清晨,他一如既往及早出门,但是再次求职未果,就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路边有一家小小的店面,门外竖着个牌子,上面随意地写了几个大字:回收灭火器。
他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忽然半路想起了什么,又退了回来,走到店里,问老板灭火器的价钱。老板回他说:“五元、十元不等,看灭火器自身的质量。”
他点点头,一路上惴惴不安的回了家,心里想着自己租的地下室角落里,那个落了厚厚一层灰的灭火器。
地下室住了很多的“北漂”,厅廊里也算是“人来人往”了,他不时地向门外张望,希望能找到个无人的空闲方便自己“动手”,但偏偏那个上午一直有人走动。忐忑不安里,好不容易盼到了中午,租客们纷纷午休的午休,外出的外出。终于,可以去偷灭火器了。
但即使没有人,他依然不敢大摇大摆的去拿灭火器。他在屋里转了半天,翻出一个大纸箱,抱着它出了门,走到离灭火器不远的地方,却不敢上前。时间过得很慢,他左看右看,生怕从哪间屋子里突然冒出个人来,汗都要淌出来了。最终,他狠了狠心,一把抓起了灭火器,塞进箱子里。
他抱着箱子找到了那家店,灭火器卖了五元钱。
我有些吃惊,问他,背上一次“小偷”的罪名,只为了换五元钱,你觉得值吗?
他看看我,想也不想地回答:“值啊!我和老婆那天的晚饭有了。”
我默默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很长时间里却忘不掉这个故事。
毕业后,大家各自谋生活,联系渐少。
三年后的一天,我搬家,路过小区门口,摆了许许多多的灭火器,忽然间想起了他,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了。只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如果混不好还可以干老本行,去餐馆端盘子。
但没想到的是,那个傍晚,居然就收到了好久不联系的他发来的短信,还有一张照片,告诉我们,他当爸爸了。
照片上的小孩很可爱,他说话一如既往的简洁,那条短信的末尾写着:母子平安,全家高兴。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