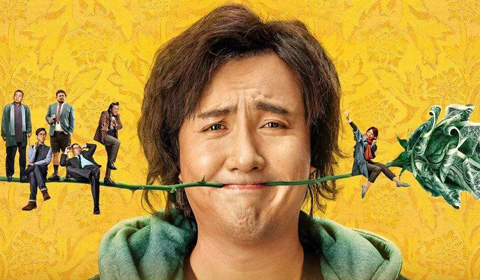有人永远18岁
在这里姑且称呼他为W吧。
嗯,那年我十七岁,在念高三,W也十八岁了,却已辍学三年。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好像好久了,很小很小,在彼此还流着鼻涕玩泥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说起来,我和W算是青梅竹马吧?毕竟我家和他家只是隔了十步,走七步,然后转弯,三步就能碰到W家的门。李白的长干行有一句很浪漫的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你也觉得很美对吗?但是W肯定读不懂,他可很不爱念书。也许就是这样,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不同的后来。
小的时候,W特别调皮,总喜欢在老街的房子东刮刮,西瞅瞅,就是为了收集老房子外面衍生出来的硝,一点燃,噼里啪啦,像糍粑兹兹作响,有几次把刘海都烧焦了。W也喜欢去田地里,打鸟,抓田鼠。在大概八九岁的时候,W拉我走到半山的一棵树下,那次他穿着一件宽宽的橙色上衣,撅着屁股,打算把树上的蜂窝捅下来。
他动作利索,很快就抱着蜂窝跳了下来,扬尘飞起,他把手伸进蜂窝里绕了一圈,然后递给我。还没等我接过来,蜜蜂便回来了,我们跑不及,结果自然是惨淡的,他被叮了好几个包,我的手背也好几天才消肿。
这可真是传说中的捅了马蜂窝啊!
过了几天,W的姑妈从香港带回来一些彩色芒果,听说连果肉都是彩色的,W豪爽地带我一起分享,我们屏住呼吸,带着神圣的崇敬感,小心地切开,其实,味道和普通的芒果没两样嘛。
日子在不经意中滑走,我们慢慢长大,上了初中,W终于长得比我高了,他总是得意地三句两句话扯到身高问题,有时候我在收晾在门口的被子,他都会突然冒出来,用骄傲的语气俯视说,要帮你收吗,晒得那么高。
我对W只剩下回忆了,可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吃鸡腿磕掉两颗门牙的滑稽样子,和他那件明亮的橙色上衣,以及他递过蜂窝时,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里面的蜂蜜很好吃。
现在的我开始无比怀念W,尽管他曾以吃糖果会长不高,骗了我好多的糖果和巧克力,我还是无比的想念他。
我上了高中,W辍学,他开始在他爸爸的工厂帮忙。我们的交流也少了起来,往往见面就是一句“放学了?”“吃饭了?”之类的简单问候,以及下雨天送我去上学时,几句简单的交谈。
我经常在想,如果W没有辍学,他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女孩子要读多点书,不要经常出去玩,不要乱交朋友。可是他自己却交上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我高一的那年,他迷上了飙车,经常和朋友在深夜寂静的马路上飞车。我劝阻他不要这样,他只是点头。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高一第一学期的寒假,因为第二天就是W的生日,我们每年都会一起庆祝,我以为今年还是这样,提着行李回家,他在擦拭他的车子。
我蹲过去问他,生日打算怎么过,他笑笑,说明天再说,我知道他又要出去了,嘱咐了一句记得小心。半夜,大概是晚上两点,我隐约听见他家的大门开开合合,却翻了个身,迷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妈妈急切地敲我房门,告诉我,W出了车祸,伤到了大脑,很严重。
果然是很严重,他弥留了一个星期,停止了心跳,期间,一直没有睁开眼睛。
他当时住的病房在十四楼,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一直让我心慌。我总是在想,如果那天拉住他,哪怕是拼了命,拉住他一起过生日,结果会不会不同?医生之前说,伤了脑,即使治好,也只是植物人,他妈妈只是哭,他爸爸则呆愣在那里。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可是奇迹只是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个星期。
W的妈妈叫我喊喊他,可我只是敢站在门口,邻床是一位伤了肺的老人,一直不停地咳,我的眼泪就这样一直流。最后的最后,我张张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在想,如果当时能喊出来,他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站起来吗?应该会吧。
其实,W只是个很平凡很平凡的普通人,他也曾偷过菜园的菜,也会顶撞父母,偶尔还会讲粗口,可是这样的他却在最后将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捐赠了出去。不是为了扬名,也不是为了能得到别人的赞赏夸耀,只是很想要他能被更多的人记住,可以有更多的人想念着他。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老去,我也可以继续认识W好多好多年,而W还年轻着,永远停留在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我忽然开始相信,星星在眨眼,石头开着花,我也始终相信,这个世界的背后会有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在平行时空的W能够一直活着,到变成八十、九十岁的皱皮老公公,也始终会幸福安康。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