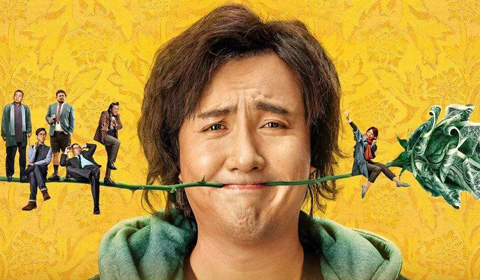追爱的人并不了解爱情
2007年,借着去北京上大学的光,我踏上了人潮汹涌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隔着涟漪丛生的玻璃看落日,望着飞速远去的庄稼,火车从大河上驶过,我终于明白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然而火车抵达首都的时候,爸爸却从电话中告诉我另一个消息——二叔和一个女人私奔了。
二叔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在言语表达方面颇具天赋。二叔毕业后回到了村里,爷爷拿出箱底不知存了多久的钱,天没亮就走着去了镇上,回来时背着一个蛇皮口袋。所有人都不知道爷爷的口袋里装着什么,爷爷始终也没有说,等到了天黑爷爷小心翼翼地来到村长家,第二天二叔就到村委会上班了,负责村委会其他人不愿意干的一切事务。
二叔在村委会工作了半年,或者说忍受了半年。以二叔的知识水平,实际上可以在村委会发挥一些作用的,而二叔每天的实际工作是沏茶倒水、打扫卫生、给村长送报纸,甚至还得回家给村长媳妇送钥匙。就这样,忽然有一天二叔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给家里人留下了一堆疑问和一张字条。
爷爷气得气管炎越来越严重,村长掐着腰说:“我们村委会是小庙,容不下你们家虎子这尊大神。”爷爷咳嗽着解释,村长摆了摆手,带着他小舅子的表弟走进了村委会,接替了二叔的工作。
初三那年,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村里,那时候在我们村别说轿车,拖拉机都是稀罕货。几乎全村人都围了上去,睁大眼睛看着,像是迎接外星人的飞船一样。这时,车门开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下车,墨镜盖住了大半张脸。村长故作镇定,走上前去跟那个男人握手,男人没有和村长握手,却递给了村长一盒烟。穿过人群,走进了爷爷的院子,只有奶奶认出了是二叔。二叔一走就是五年,几乎把奶奶的泪水耗尽。
二叔衣锦还乡,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了,从此隔壁班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个很厉害的叔叔,老师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从那天起,上门来给二叔介绍对象的人络绎不绝,爷爷奶奶很开心,二叔却对此无动于衷。
有天晚上,二叔拿出一根英雄钢笔塞给我,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去外面看看。“待在这里,你的眼界会永远那么窄。”说这话的时候,二叔望着圆圆的月亮,眼睛中似乎有泪光在闪动。我知道,外面虽然很美,但要想活得很美,必须付出无尽的艰辛,尤其是对于一个外乡人。当然,这是我来到首都求学之后体会到的,明白了二叔在南方一定很不容易。那晚,我们聊到了后半夜,二叔提到了一个姑娘,他们相恋过,最后被人用一套房子诱惑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二叔认真聊天。
几天后,二叔娶了一个村里的姑娘,婚礼办得很隆重,二叔把汽车后备箱带回来的香烟都散尽了。晚上,二叔喝得酩酊大醉,拽着我说了很多话,让我抓不着重点。但我清楚的记得,二叔在说一句话的时候,目光如炬,甚至摔了一个酒瓶子,他说:“趁着年轻,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只有拼过了,才知道它到底属不属于你。”说完二叔就溜到了桌子下面,自顾自睡着了。
二婶是个典型的乡村式贤妻良母,从不多说少道,衣着朴素,做得一手好菜,只是相貌平平,没上过学,对于她来说,我们镇就是整个世界。没见过夜空中闪动的霓虹,没嗅过芬芳的玫瑰,更没品过甘甜的红酒。她认为,只要好好侍奉二叔,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准点做饭,到时给二叔生个孩子,这样就是永远了。她无论如何看不到二叔以梦为马的心,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读懂二叔的心。
有阵子,二叔异常忙碌,说是在外面倒腾药材。只有我知道,二叔出去赚钱不假,还有就是去找他爱的女人了。二叔的车上有个漂亮的汽车模型,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两眼冒光,被二叔轻易识破了。二叔笑着说:“下次回来,我给你另买一个,这个不能送你。”那是他和她在规划未来的时候准备买的一款车,那时候二叔还是一贫如洗,那辆车对于他来说有些遥不可及,如今二叔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它,她却坐进了更贵的车里。
这些事情是那晚二叔告诉我的,大家看到了二叔的汽车、西装还有包装华丽的烟和酒,却没有看到二叔那颗被撕碎的心。回来后,二叔和别人对外面的事情只字未提,总是招呼大家抽烟喝酒,而这背后的东西二叔只告诉了我。二叔说家里只有你能交流,只有你能理解我,我曾以此为荣。很多时候,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去探求真相,心里痒得很,当你知道真相后,心里痛得很。
二叔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些礼物,起初我以为他是为了“收买”我,我也信誓旦旦地跟二叔表态:“二叔,这些事情,我会装在心里,烂在心里。”二叔笑笑说:“孩子,这些东西不值钱,我也不指望拿这些东西堵住你的嘴。你帮我分担了忧伤,理应得到这些。而且,我是为了让你知道,二叔一直在努力着。”
我得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汽车模型,但我从来没有打开包装,像是尘封自己的心一样把它一直放在床底下。有时候,我会把它抱出来,细细端详,想象着二叔开车带着她兜风,聊着、快乐着。这时,一辆宝马开过来,她毅然下了车,坐进了宝马里,留下了二叔一个人。我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二叔的事情一度让我不安。即便是她回心转意了,又能怎么样?在我们村里,没有人会关注原因,只要是离婚了,就是伤风败俗,就是不肖子孙。更何况二婶的人品人尽皆知,有目共睹,虽谈不上知书,但是真正的达理。我曾一度想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在同情二婶的同时,更同情二叔。
那段日子,二叔明显苍老了,奶奶说:“钱赚的够花就行,房子也盖起来了,生个孩子,再某个安稳的营生,好好过日子,别让自己太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二叔高兴极了,给了我一个大红包。
临上火车前,二叔把他的一块手表塞给了我,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的深邃而有深意。家里人都在,我没敢提二叔和她的事情,只是对他说:“二叔,你要保重!”
可我刚抵达首都,二叔就带着她跑了。
她的男人来到了村里,话说得极难听。爷爷和爸爸愤怒了,妈妈惊讶得不知所措,二婶扶着奶奶哭得死去活来。我听后很镇定,告诉爸爸:“过一阵子,他可能就回来了。”爸爸在电话那头骂了许久,我无话可说。
一直到放寒假,为了多赚些钱,我到了春节临近才回家。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都笑着,但是没有人提及二叔,仿佛是种禁忌一样。二婶做饭依旧很香,对我依旧很好,眼睛里却带着一眼看出的空洞。一开始奶奶抱着二婶哭,后来二婶不哭了,奶奶还哭,就这样坚持了许久。
我把二叔带回来的音乐盒送给了二婶,里面的音乐是《梦中的婚礼》。我说:“婶子,这时学校奖励给我的,你烦闷的时候听听吧。”
整个寒假,二婶都表现得很平静,炸黄鱼给我吃。临回学校的时候,我去跟二婶道别,二婶把二叔留下的烟塞给了我:“在外面用得上,外面的人认这个。”我说我不抽烟,二婶说:“有人抽,送给抽烟的人,多个朋友多条路。你不喜欢的事情很多,但这不能阻碍别人喜欢,送给他喜欢的东西,他就是自己人了。”说着二婶打开柜子说:“你二叔喜欢抽的烟我给他留着呢,他喜欢买几种烟,但是他自己只抽这种。他只是一时走错了路,他会回来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二婶异常坚定,仿佛二叔已经站在了村口。
那是二婶第一次说那么多话,句句皆是教诲。我以为二婶只会烧火做饭,擦桌子扫地,而她心里的参天大树,是我遥不可及的,只能仰望的。照此来想,二叔的事情二婶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只是二婶忍辱负重,选择了沉默和短暂的纵容而已。
回到学校,我点了一支烟,熏得眼泪直流,整理好思路,走向电话亭,给二婶打了个电话,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关于此事,二婶没有表现出诧异,更没有多谈,而是告诉我在外面要注意身体,结交好的朋友。我难受得很,却不知道是自己难受,还是在替二婶难受。
2008年,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盛况空前。我有幸成为一名媒体村志愿者。一天下午,有位伊朗记者给了我两块饼干,我正在考虑吃还是不吃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二婶,话语很简短:“你二叔回来了,有时间就回来看看吧。”说完就挂了。感觉像是预言家在指着一堆废墟说:“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几分钟后,我接到了爸爸的电话,二叔果然成了“废墟”。
如今的二叔坐着轮椅,半个身子不能动弹,说话含糊不清。他是被抬着送回来的,送他回来的别克商务车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人,却始终都没有下车。二婶叫上爸爸和几个叔叔,把二叔抬回了自己家。那天的雨,下了一夜。
我见到二叔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了,那个音乐盒摆在二叔身后的桌子上,他看见我进来,异常激动,嘴里像是在说着什么。二婶解释道:“你二叔让你坐下喝点水。”我坐下来,握着二叔的手,打开音乐盒,《梦中的婚礼》奏响了。一曲完毕,我对二叔说:“叔,二婶等了你那么久,不容易,到头来照顾你的还是她。”二叔拼命点头,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地滑下来,二叔多数时候是自信的,是趾高气昂的,是不服输的,这次二叔哭得低下了头。
二叔因为脑溢血险些要了命,送到医院还算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是自己无法走动,说话也不清楚了,医生说有恢复的可能,就看自己的造化。
二叔开着本田走的,坐着轮椅回来的。他在她身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投入了多少心血,用二叔的话说“就差把心掏出来,跪在地上求她了。”
二叔走后不久,二婶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自己养活着,娘家人愤愤不平,全被二婶堵了回去,二婶底气十足地说:“我嫁到了这家,就是这家的人,无论怎么样我都认了,你们不许搀和。”奶奶听了,偷偷地哭了。晚上,奶奶一个人坐在桥头,唤着二叔的名字,村里人都以为奶奶急疯了。二婶每天做饭、种地、养猪,一样也没有耽误,儿子养得白白胖胖,只是二婶的话更少了,唯一的几句话只是对儿子说的。皇天不负有心人,二婶把二叔等回来了,可惜等回来一个残废。
我以为二婶会大哭大闹,甚至精神崩溃。爷爷说,二叔回来后,二婶冒着雨把二叔接了回去。给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把身上的衣服扔在了外面,立刻烧水给二叔洗了个热水澡。二婶把儿子抱到了二叔面前,孩子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二叔也含糊不清地说着,只有二婶一个人听懂了。
第二天,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二婶把二叔推到了院子里透气。从此,二婶成了二叔的翻译,几乎形影不离。二叔私奔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奔波,回来后白天在爷爷家待着,只有晚上才回去睡觉,几乎没有见过二叔和二婶聊天,甚至连吵架也没有。没有交流,怎么会吵架呢?
二叔真正离不开二婶了,我却为二婶感到可惜。村子里的很多人也偷偷地劝二婶改嫁。二婶听后只是一笑,仍旧是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二叔,比以前照顾得更好。为此,二婶的娘家都和她翻了脸。
两年后,二叔去世,二婶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人笑话她,在任何人眼里二婶都做得仁至义尽。二叔如愿以偿地听到了孩子叫他爸爸,笑着走了。
后来,二婶一直没有改嫁,奶奶也曾劝过她,二婶二话没说就给拒绝了。
清明回去上坟,二叔的坟旁开满了小花,村里人说那是二婶特意种的。
我给二叔带去了他最喜欢的烟和酒,把烟点上,把酒倒在了坟前。把那个一直没有开封的汽车模型打开了,摆在了坟前。
二叔活得不算久,挣了好多钱,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让她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二叔开着本田,最后坐进了轮椅,这两样东西村里的很多人没坐过,甚至没见过。二叔的成功,曾一度让村长对爷爷刮目相看,春节送来米和面,说是慰问群众。村里很多人结婚都让二叔去当证婚人,说着铿锵的话语。二叔的坟是村里第一个完全用水泥砌的,后面还有墓志铭。二叔死后,有个陌生的女人开车来为他祭奠,坟前摆的贡品不亚于过年的礼品,可能只为讨个心安。然而这一切,都在二叔去世后化为泡影,变得毫无意义。
只有二婶,实实在在地陪伴二叔过完了最艰难的岁月,为二叔把唯一的儿子抚养成人。自始至终,二叔可能都没有爱过二婶。在这一纸婚约里,二叔屡屡犯纪,二婶靠着良心的自我约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我坐在二叔的坟前,问二叔:“二叔,你以为你一直苦苦追求的,就是真爱吗?你以为奋不顾身的才是爱情吗?”没有人回答我。
所有的激情澎湃和轰轰烈烈,最后都会转为平淡。能在茶米油盐、索然寡味中与你长相厮守,不离不弃,打不离吵不散的,才是真爱。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