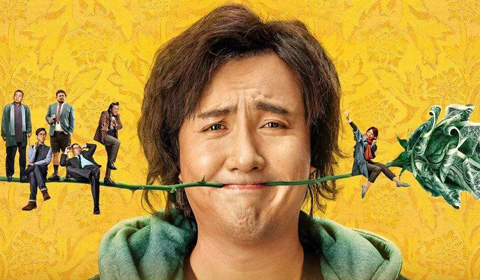追风啦少年
2003,非典肆虐的那一年,我才读五年级,放了人生有始以来最长的一次假,六十天,每天写着份量多到惨无人道的作业,从来没睡过好觉。
我是H省人,户口所在地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从小到大没发觉我们比别人穷在哪里,只知道县里三十年难得出一个清华北大,县长会亲自敲锣打鼓把锦旗和十万块送到状元家。
这种境界,估计比天方夜谭也就只欠一点神话色彩。
一个教育前景凄凉的地方,你永远无法估量孩子的成长能有多残忍。
升初中的时候,我考了全县第三,我爸不知道托了多少关系才把我连押带捆在半年后扭送到著名的魔鬼班。
那个新班主任,性别女,爱好钱,特点狠毒,技能是虐出全县第一的“人才”。每年都有学生熬不过去,像精神分裂一样被从她班里送走回家休养,但是每年都有铺天盖地的家长抢破头要把自家儿女送去给人虐。因为全县人民都知道,她带的班,十年来打遍全县无敌手,只有她班里每年会有个别人能进入省城读高中,也才有更大的希望在百万考生中成为红榜高中的个位数。
从小算得上品学兼优的我在那个班,第一次因为做题速度慢被人一脚踹进垃圾桶,第一次因为一本书随意翻开某页背漏了几个字而没机会回家吃只有五分钟时间的饭,也第一次因为在同学嘴里问不出作业被扔到角落一整天。
从此后,我每天不眠不休,直到一场考试可以十分钟交卷还保证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正确率,直到背书快到让检查的人目不暇接,直到成为那个女人眼里红透半边天的好学生。
当我知道我们高傲的班长、我小学的同桌破天荒来打听我的心事,是为了报告给她,从而令我在最初的时候身为新生几乎寸步难行,我再也没有向谁说一句多余的言语——我和她认识那么多年,她只做过这一件事令我自戳双眼刮目相看。
我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市里的仅有的七个学生之一,并且成功瘦得好像被黄鼠狼啃过的鸡骨头。
这些年,很多成功人士都爱说,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相信,但是who care?
那又怎样——你永远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我只记得,毕业的时候,我在那里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三年的同学面对面,只留下客套与生疏,没有一点高升的喜悦。
离别,没有不舍,就像逃脱。
记得当年,从前的班主任带着同学们的关心来看我,眼泪掉下来糊了满脸,后来当时的好友兼同学告诉我,班主任回去说我哭了,班里那一天分外沉默。
我那时候还相信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世界是美好的。
到十几年后我也未能忘却那段惨淡的岁月,然而我知道,就算我后来自甘堕落,我爸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忘,逢年过节给那个靠我多拿了一千块奖金的女人在心里默默上三柱香烟。
那年我十三,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去了山脚下的那所市立学校,带着低到随时会休克的低血压和贫血,还有一身疲惫。
在那个交通不发达、十块钱都算贵的年代,天知道几百里地在一个傻乎乎的小孩眼里有多遥远。
那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新世界。
各个地方的学生,各形各状的人,还有,各种矛盾。
小女生总会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刁钻,而什么都不懂的人总是容易被欺负得更惨。有段时间,看到女生我都会害怕得哆嗦。我真心想不通人它妈怎么能把人生得那么复杂。
新的班主任喜欢掌控一切,用各种方法监控我们,每天顶着他充满阴谋论的眼神就像背上有座随时会喷发的活火山。
那个时候理科很火,老师把唯有的几个打算学文的学生打压得很惨,我拼命学物理却只考了十几分,一学期进了五十二次办公室还一直坚定地说我不学文才逃过一劫。
也许我自己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起当年那个女人鲜红的口绽开好似狰狞的笑,还有日复一日诵经般的背书声。
我爸那时候脾气很差,说话梗得人听不下去,极其信奉棍棒教育,对我下手从不留情。他总是一边骂我无能一边怀疑我有多恶劣,我什么都不敢说也不能说,或者说了也没有用。
同来的六个人,忙恋爱的忙恋爱,不忙恋爱的忙学习,还有的忙着迷恋学校那些不良少年关于哥的传说。只剩我一个,忙着发呆,不知所措。
白天黑夜,我爬到篮球场最高的台阶,看脚下星星点点散落的建筑和灯火,唱歌,写字,或者沉默。那里安静宁谧得像我心里家的味道,多黑暗多孤独仿佛都不会畏缩。
我一直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一个人的景听一个人的风,直到,开始有一个人,给我回复。
他大我三届,面临莘莘学子最难跨越的那道天堑。
那时的我们,谁都没有听说过笔友,也许知道了也算不上,我们从不联系,连名字都是假的,就只守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你一言我一语,似乎就算相见亦不相识才会安心。
但我知道,那是不一样的存在。
因为,相信。
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很难付予,有时候却给得那么轻易。
我用尽一切心力维护那个地方,雨天为它撑伞,冒雪为它扫冰,仿若寄托全部的痴迷。
For how much I love you.
我偷偷叫它,忘乡。
那是遗忘的地方。
给我教诲和安慰的那个人,我把他当作生命中值得依靠的长者和知己,甚至为了只言片语彻夜在音乐教室学他心痛放弃的钢琴。
当时年少,我以为的青梅煮酒,笑傲江湖,还没有剥落纸造的彩衣。
时不我待,到了分科的时候,我终于再也逃不了。
我爸气势汹汹地杀到学校,我妈又哭又闹,还夹带着班主任在一旁阴森的冷笑。
我想不到年少怎会那般脆弱,但是我知道,我当时,甚至真的想过死亡来解脱。
十四年的时光,我都不懂活着为了什么,痛苦,或者迷茫?最后为了一点责任苟活。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的师兄,那个人再次参加了高考。他考得很不好,那个结局偏离了所有轨道。他从前那么优秀,却还是成了千万无名小卒中的一个。
他临走前,我去送他。
第一次见面,白衬衫,牛仔裤,明净的脸庞,清澈的天光,符合所有狗血言情剧的场合。
他说,什么朋友,都是假的,一时的放松而已。
我只是笑,一直笑,一滴眼泪都不想掉。
我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清清楚楚听到我妈说,你劝劝她。
大约是因为那与我同来的六个中有一个终于忍不住,告诉我父亲我的境况而我却固执不肯转学回家的缘故。
我从小就倔,不肯轻易认输,却没想到他们居然想到去找他。
很显然,我爸又偷看了我的日记,或许已经撕掉了,而且是我妈告的密。
我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不会原谅他。
就为那句话,就为他说过我理解啊。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提他。
后来,过于糟糕的精神状况引发了家族的遗传病。我终于也离开了那里。
一年后,我在新的学校再次满血,恢复得一点看不出刚开始自闭又阴郁的模样。
我从来不刻意掩饰那些过去的事情,因为只有愧疚和自卑才会对往事逃避和深晦,而我从来无愧亦无悔。
有时候我会骗人说那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个看客——我想面对那些复杂的目光挺直脊背。
在新班级里混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几乎算得上陌生的班里一个人寄来的留言。
他说,我一直在看着你。
就像忽然间的记忆回溯,我突然想起有那么一个人。
我那时候还很傻。
他坐在我旁边,隔着一个走道,长得白白嫩嫩的,喜欢侧着脸笑。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你就会看到我的酒窝。
他也挺傻,我不知道我要看他的酒窝干什么。
他说,很多人都在猜那个台阶的字是谁在写,是你吧。
他说,我在你身后跟了你很久。
他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
取次花丛懒回顾。
他一直望着我,我却一直望着不属于我的黑白琴键,恍然如梦。
我没有回答。
对我而言,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故事,旧到不必再说。
那个班这些年的同学聚会我一次都没去过,但是那个在身后陪我默默走过无数黑夜的十五岁的少年,我总是想到他就想要微笑。
现在有谁还会执著于去做帮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事情?于是即使那一束我错过良久的光,我仍然读到了希望。
七年之后,我在山的另一边写下这些年少时遗忘在风中的故事。这时我才明白这世上原来还有个东西叫考研。
我依然怀念那个有风的寂寞高阶,却不再执著于当年。
半缘修道半缘君。
送给曾经追风的少年。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