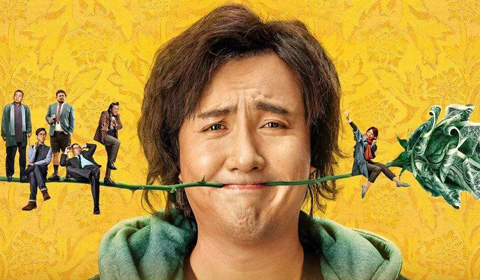柱公的桔子
我读初中那会,桑婆还会走路,还会和挑着小担的柱公一起走去镇上赶集。有时候星期五回家,桑婆看见我,还会像小时候一样招呼我,用她独一无二的爱称“tīn tīn”。她喊不来我的名字“婷婷”——这个当时在小村子里因为没有对应方言显得还挺洋气的名儿,总是笑着用第一声喊我,听起来就是“tīn tīn”,也称呼也成了她的专属。
后来,桑婆生病瘫痪了。于是每个赶集日的泥土路上再没有她的脚印,只有柱公一人,仍是挑着小担,或是一筐青菜,一挑萝卜,一袋他自己晒的笋干。鸡蛋也有,但好像少了。听奶奶说,他每天都给桑婆煮一个鸡蛋。有时候水炖,有时候刮点猪油煎,自己大多就胡乱炖个土豆南瓜之类的。
他喂她吃饭,却也慢慢熟练了起来,轻声细语地哄:“桑娥,咱家老母鸡每天都生蛋,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就一天吃一个,就能走路了。”
有一回傍晚,我妈让我送菜给柱公。他正在破旧的土坯厨房起火,乌漆抹黑的小破屋子,牵着蜘蛛网的灯泡和电线,昏暗的连凑在眼前的人脸也不怎么能看得清的灯光,一旁老式竹背椅上桑婆的一头白发,我心里发怵,跟柱公说了一声就赶紧往回跑,也再没听过偶尔坐在院子里的桑婆喊我“tīn tīn”。
乡下人起得早,柱公更是。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把桑婆抱出房间放竹背椅上,给她刷牙洗脸喂饭,然后自己扒两口饭,扛起锄头挽着裤腿下田里干活。有时候柱公活多,天快黑了还没回来,桑婆会一声声地喊,“柱……柱……”
那时候她基本上已经说不清楚话,就那么喊着。有时候是饿了,有时候是冷了,有时候是想上厕所,有时候,也许就是担心了吧。听家里人讲的时候,似乎桑婆的喊就在耳边绕,远远地好像看见挽着裤腿的柱公从那小坡上走下来,扛着锄头,瘦黑的腿,溅起的泥,疲累的脸。
后来高中的一天,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她说桑婆过世了。那天傍晚,柱公回家发现桑婆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一慌,赶紧跑到隔壁小儿子家。儿子不在,儿媳妇冷眼说,“死了就死了,瘫这么多年……”柱公什么话也没说,只回去把桑婆抱回房间,生火烧水给她擦了身体,换了干净的衣服。那一晚过得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一早,柱公到隔壁喊了尾叔帮忙。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大家到的时候三个儿子和儿媳妇已经跪成一片,哭天喊地,说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丧礼办完之后,隔壁的小儿子让柱公去他家吃饭。只是第三天的傍晚,柱公黑漆漆的土坯厨房又开始飘起了炊烟。听说那两天他是一个人坐在院廊的板凳上,用着专门的一副碗筷,吃着剩菜剩饭。有邻居路过,和他聊起,他淡淡地说,“我桑娥走了也好。”
后来,还是能经常看见柱公走进他小儿子家的院子。有时候捧一把空心菜,有时候提一个葫芦瓜,抓一把茄子。
也还是能经常看见他挽着裤腿,扛着锄头从那小坡上下来。我喊他,他每每都回,“哎,读书放假啦?”有一回我妈开着摩托碰见赶集回来的柱公,瘦黑的小老头,挑着担子,就让我下车自己走回去,她载了柱公回去。我到家的时候,正巧碰见柱公拿着一袋桔子和我妈推来推去。
“柱公,你老人也没什么东西,就留着自己口渴吃。干嘛还特意再送过来。”“也没什么东西,两个桔子给tīn tīn吃。”怕妈妈不要,他扔下桔子就跑了。我听着他说的“tīn tīn”,看着他真的是用跑的下我家门前那个坡,忍不住一阵眼睛红。袋子里的桔子参差不齐,有小个的,有干蔫的,但他一定是挑了最好的了。
再后来,妈妈有天打电话说老人走了,正在办丧礼。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