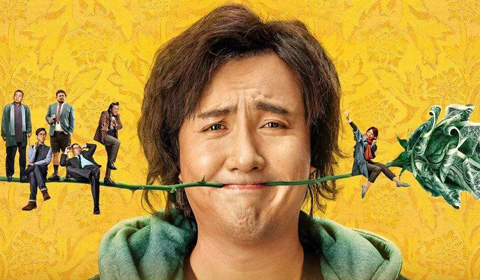如果有圣诞老人
大学毕业那年我不满22岁,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里毛手毛脚的小编辑。初来北京的半月,不争气地我每天都哭,只因为一个很滑稽的理由:我路痴到这种程度,刚租的房子,每天下班都找不到家在哪里! 但是我白痴的北漂生活很快就结束了。23岁那年,我告别刚刚开启的图书编辑生涯,满怀好奇的奔赴英国留学。这是个随时能让我在心底发出感叹号的国度,无论是辩论的议员,还是谈论亨利王子裸照的街头男女,都用一种歌剧家的喉咙,吟诗般的语调在说话。 不过,我的班级并不是典型的“英国课堂”,班级里大部分是亚洲人,中国人尤其多。我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得刻意避开国人的圈子去混社团。可英国的社团每周一次,结束后谁都不记得谁。因此,来英国半年,我始终是可怜巴巴的一个人。一个人煮意面一个人去超市一个人逛博物馆……像个孤单的游魂。 那年的圣诞节很快就到了,街道上的彩灯和装饰一天天多起来,节日的氛围扑面而来,我独自走在热闹的街头,感觉凄凄惨惨戚戚。想象着不久之后的圣诞节,我一个人为自己唱圣诞歌的冷清画面,在心底一遍遍说NO。 终于,在一个漫长的黑夜,我边在HostUK网上申请去英国寄宿家庭短住,边祈求着,如果有圣诞老人,请一定给我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吧! 没多久,真的就有一封邮件躺在了我的邮箱里,像是圣诞老人提前送了我礼物。有一家来自Brixham小镇的爷爷奶奶决定“收留我”去他们家过圣诞了!奶奶还特意发邮件来说,他们几年前才结婚,两边子女非常多,孙子孙女就有13个,是个非常大的家庭。 我拿着一张Brixham的火车票,怀着小小的忐忑踏上了旅程。但没想到,路途遇到洪水,火车走走停停蜿蜒前行,八小时后,才终于在Brixham的火车站停了下来。 天已经全黑,浑身感觉冷飕飕的。但别人看上去心情似乎不错,大概因为要圣诞节了,一个个冲出火车就跑了起来,唯有我迷茫地打量着这个小镇。 很快,我发现了一个银白头发、带着圆片眼镜、穿着红色衣服的爷爷,看上去有七八十岁,个子高高的,背也非常直,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好像一个圣诞老爷爷。 他笑眯眯地说你是Kia吗?我清醒过来,说是呀,你就是Tony吧!他笑了,边点头边接我手上的行李。 爷爷的太太Sue就等在车旁,她圆胖的身子裹着碎花连衣裙,眼睛也是圆圆的,整个人神采奕奕,特别活泼,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就不停地说话。 我坐着爷爷奶奶的车回家,车一直神奇地在山上跑,另一侧是黑黝黝的大海,奶奶把车开得飞快,大概过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在了山顶的一座红砖二层小楼前。 那是我第一次住传统的英式家庭,感觉像是穿越到了影视剧里。进门就看到哈利.波特住的那种壁橱上挂满盖着世界各地邮戳的圣诞卡片,左侧门通往客厅,墨绿的棉布沙发、厚厚的灰羊毛地毯、黑铜雕花壁炉、老式电视机,镶扣红棕皮躺椅,整面墙的落地窗下摆满CD和书的柜子以及圣诞树下堆着的礼物,让我有“这才是英国呀”的真切感受。 奶奶风一般从厨房端出早已准备好的鸡肉派,糯米布丁、烤面包,叮叮当当的刀叉盆罐声中,她给我说起他们的故事。 那时我才知道,虽然他们七八年前才结婚,却是从年轻时就相爱了。 两个老人的故事,像是BBC的午间剧场,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当时Tony和Sue还是一对普通的情侣,相处甜蜜,谈婚论嫁。但是,当时的北爱尔兰总有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两人在战争中失散了,再也找不到彼此的消息。很多年后,爷爷娶了妻子,奶奶也嫁了人。 一晃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而就在几年前,奶奶居然在电视台一档地方节目上看到了爷爷。而且时隔多年,奶奶一眼就认出了他来。那时候,奶奶已经离婚多年,爷爷的妻子已经过世。奶奶看着电视上的爷爷,很快给他写了封信去,第一句话就是:嗨,托尼,你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隔了几十年之后,爷爷奶奶终于再见面了。他们发现,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而且和当年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没多久,爷爷卖掉了在约克的房子,在Brixham这个海滨小镇和奶奶重新组建了家庭。 结婚那天,七十四岁的Sue带着孔雀尾小礼帽,和八十岁身着礼服的Tony很相称。双方的七个孩子和十三个孙子孙女们加上亲戚朋友把小镇教堂塞得满满当当! 两位老人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又幸福地在一起了。 而这对非凡的老夫妇,也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在一起生活乐趣十足。早晨醒来,和厨房忙碌的奶奶打招呼,会遇到松鼠从院子外的森林中,踩着树顶小径蹦跶到院子,在爷爷特意为它们制的秋千上玩耍一番。午饭后,帮忙做家务时,爷爷还会耐心对我讲洗碗机的运作方式。 爷爷的家外面是悬崖,悬崖底下就是大西洋。吃完饭,爷爷会很绅士地提议说:“不如我们去散步吧?”他就领着我和另一个寄宿的土耳其女孩,走几步转个弯,踏上了悬崖边旁的林荫路,吹着大西洋来的风,看着浪涛拍岸,我在心里感叹,这真是“高规格”的散步呀。 住了几天,慢慢摸清爷爷的习惯,比如他的作息十分规律,每日中午必在院中的阳光房打个盹,醒来便慢调思理地煮咖啡,因为“天大的事,不如来杯咖啡吧。”再比如他的脑子总是能蹦出一串新主意,无论是几十年前为了娶妻自己组装的汽车,还是世界旅行。他嘲讽自己总是:“Doit,seewhathappens.” 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日子过得飞快,平安夜到来了。我按捺不住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连夜画了六副画。有家乡厦门的风景,也有这个海边小镇,我将画拼成一个多面体,包装好悄悄放在了圣诞树下。而第二天早晨,我竟然发现床边多了一双缝着我名字的圣诞节靴子,里面鼓鼓囊囊塞着十几个包装精美的小礼物,是奶奶亲手缝制的! 一大早我飞奔到厨房拥抱感谢奶奶,她边穿着鲜紫色的礼服,边开心地说:“今天你的任务是当邮差!” 奶奶又一阵风似的飙起车,载着我在山上的社区里来回转着圈。每到一家,我便敲开主人的门,送上圣诞卡片和祝福。在养老院和独居老人的家,奶奶把亲手织的画和各种小玩意儿送给老人,并相邀接她们圣诞节到家中玩。 上午十点,教堂钟声响起。奶奶把我放进一群穿着天使、牧人服装的孩子中,便急急去做礼拜的准备。我还在和孩子们闹,没想到一个阿姨急急抓住我问,你能顶替一个未到场的人来参加圣诞吟颂吗?于是,在爷爷奶奶惊讶的目光中,我登上演讲台,大声朗诵着临时抱佛脚向小妹妹学来的圣诞故事篇章,心底无限快活。 礼拜后刚回到家,大大小小送祝福的朋友就都来了,比在家乡过年还热闹,还有圣诞老人打扮的邻居。他们驱车从耶路撒冷采来火种,放在油灯里,在圣诞节的早晨分送到各家各户。(取自圣经中将耶稣比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之意) 圣诞的夜晚,爷爷拿出一个录像带,录着一部著名的圣诞动画《雪人》。我们坐在沙发上,挑选好最舒服的位置,奶奶端来了香气四溢的咖啡甜点。看完动画片,奶奶又放了一部纪录片,讲阿富汗发生战争时,阿富汗军嫂组织了一个合唱班的故事。合唱班唱了许多温暖动人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最为特别,军嫂们每人说一句最想对老公讲的话,这些话拼起来就成了那首歌的歌词,音乐老师谱上曲,那首歌也成了当年圣诞节最受欢迎的曲子。 其实和爷爷奶奶度过的圣诞节很平淡,但这种平淡里的温暖却是我在英国很长时间里最大的慰藉。短暂的圣诞节很快就过去了,我离开了那两位可爱的老人,但后来的我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有一份惦记:那个英国西南角的小镇,一片大海,一处悬崖,一片森林,还有松鼠的陪伴和咖啡香气中那对恩爱的老夫妇。 我一直念念不忘小镇爷爷奶奶,为了将Tony和Sue的故事说给别人,我特意参加了“生命写作课”,和一群六七十岁的奶奶们一起写、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个个经历曲折,有人从阿富汗战场死里逃生,有人跨越几个国度,也有人是身患癌症的巴西心理学家,我是最小的学员,与他们相比,我才23年的人生毫不丰富和曲折。 但是我有着一个和一对传奇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圣诞节,这是我留学生涯里最温暖美好的一页,也是我坚信的圣诞老人送来的最好的礼物!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