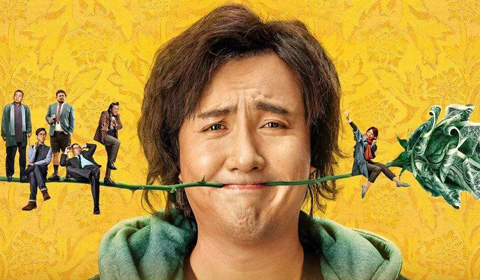亲情无限无限:不忍忘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六个年头了。
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剪头时的情形。
从六七岁开始,我和哥哥的头发就被父亲“承包”了,每当头发长长的时候,父亲就一声不响地找出推子,抓过正玩儿得热火朝天的我或哥哥,摁在板凳上,也不问我们喜欢什么发型,只管按着他的“构思”施展身手。
父亲剪头一丝不苟,可能是想通过我们的脑袋把他“高超”的手艺表现开来吧,他通常是左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右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接下来左边剪几下,后退几步,右边剪几下,后退几步……直到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快坐不住的时候,父亲才收住推子,站在我们的正前方,咪起眼睛边洋洋自得地边欣赏边点头,最后,父亲会替我们解下围巾,吹净头发茬儿,拍拍我们的脑袋喝道:滚蛋!我们就顶着父亲的“杰作”又到外边疯跑去了。父亲最拿手的发型有两种,一种是“茶壶盖”,一种是光头,父亲剪的光头锃明瓦亮,宛如200度大灯泡一般,于是邻里人都知道:文明他爸剪得一手好头!
十三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乡初中,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开学的头一天按惯例父亲该给我剪头了,可他却迟迟没了动静。我暗暗称奇:难道父亲又在构思什么新潮发型吗?下午,父亲叫过我,递给我一块钱说:“找个理发店把头剪了,剪个分头,精精神神的,上乡初中了,人家那地方不时兴茶壶盖。”于是,从那个下午,我便告别了陪伴我儿时的“茶壶盖”。
我们那儿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人多地少,风调雨顺时能多收三五斗,年头不好时就愁煞人。那时我们姐弟三个都在念书,一年的花销全靠父母从几亩地里刨出来,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但在供我们念书这件事情上父亲却从没动摇过。我家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买自行车家庭中的一个,那时买一辆自行车需一百五十多块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父亲却毫不犹豫地买了,就为我上乡初中要走十几里的路。有时快开学了,我们姐弟三个还没有上学的费用,父亲就明显地沉默了,家里的气氛也格外压抑。父亲或屋里屋外地走动,或一声不响地去别人家。最晚在开学的头天晚上,父亲会把我们叫到跟前,神气十足地把每个人上学的费用拿出来,嘱咐我们搁好。那时的父亲又像给我们剪完头时那样自信,底气十足。只是我们不知道父亲为那些费用借了多少家,看了多少人的脸色,说了多少好话。
苦读三年,我考上了高中。上学的费用由几十元一下子变成了几百元,那可难住了父亲。连续几年的大旱,地里没有收入,沉重的负担已压得父母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几百元的费用又像山一样挡在父亲面前。那些天,父亲坐卧不宁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剪头时我坐在板凳上的样子:热锅上的蚂蚁。
村里的同龄人几乎都辍学打工去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他们一样。一天早晨,父亲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早饭都没吃就套上驴和骡子赶车出门了,下午才回来,回来时只有骡子孤零零的拉着车——父亲把耕地用的驴卖了!那天父亲没吃晚饭就早早地睡了,第二天醒来我偷偷地望过去,发现父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
求学的日子依然清苦,家庭的负担依然沉重。高二下学期的一天,父亲托大姑给我捎来十七块钱。家庭生活很富裕的表妹挺纳闷:怎么会捎十七块钱呢?至少应该是个整数吧。大姑告诉我:这十七块钱是父亲把二月二留着吃的猪头卖给村委会了。生活富裕的表妹也许永远想不明白,其实,父亲何尝不想捎个整数呀!
劳累和苦闷使父亲过早地苍老了,四十几岁的人就像个“小老头”。有时放假回家,我提出让父亲给我剪头,父亲就会摆摆手说:“扯淡,都啥年月了还剪‘茶壶盖’?”可是我知道那把推子父亲一直没扔,有时他会悄悄拿出来躲在角落一遍一遍地擦,擦完了偶尔还一个人比划着剪头的动作,闭上眼睛听推子“咔嚓咔嚓”的响声。我想,父亲留恋的,不仅仅是他曾经在我们头上的“杰作”吧!
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
我回到村里,悄悄地去了一个姓盛的包工头家,让他带我上砖厂打工。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姓盛的包工头去找我,父亲知道了,斩钉截铁地说:“哪儿也不去,还得念书!”
父亲那句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父亲是在我复读那年的八月离去的。其实父亲的病头几年就有征兆了,只是他一直没有说,一直苦苦地撑着,苦苦地撑着。
这些我都不知道。就像我永远不知道父亲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一样!
考学,苦读,毕业找工作……一个人在他乡,很苦很累,只是我学会了咬紧牙,俯下身子坚韧前行。
我不敢松懈自己。
这几年我一直剪短发,很短很短,酷似“茶壶盖”或光头。每当坐下来理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情景:父亲抓过正玩儿的热火朝天的我或哥哥,摁在板凳上,也不问我们喜欢什么发型,只管按着他的“构思” 施展身手。他左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右边剪几下,停下来后退几步,咪起眼睛仔细端详,接下来左边剪几下,后退几步,右边剪几下,后退几步……
有些东西,是一生都不忍忘却的。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