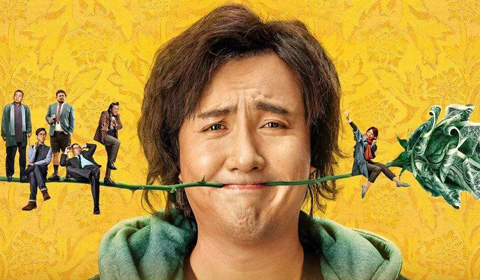我的隐秘而伟大
爸爸是个铁匠。
没错,就是那种拿着四十公斤小铁锤,六十公斤大铁锤每天对着炉火敲打锻造的铁匠。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有人问起爸爸的职业,我总是说爸爸是位理发师。
没错,爸爸确实也是一位理发师,在我三岁那年离开家乡前是,到沿海城市驻扎十几年来也是。可什么时候,拿着小小的剪刀在别人头顶上小心翼翼剪出漂亮发型的爸爸,就变成抡铁锤的铁匠了?
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回了趟老家四川,在这之前由于高考失利我踏上了北上的求学路,连续两个春节都是独自一人在异乡度过。因为大学离家太远,而回家的路费对于家里来说是极高的,甚至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爷爷离开人世时我也没见上他最后一面。
是的,曾经我是留守儿童中的一员,爷爷是陪着我长大的那个人。
爷爷的离世让本来就不热闹的家只剩下年过九旬的奶奶和小叔两人。我此行也是待不久的,按照计划,待一段时间后我就要到爸妈打工的城市做段暑假工,然后开学时再回到学校。
记得从老家出发那天,几个叔叔和堂哥都送我上大巴车。等车的间隙,惦记着爸妈的电话,但不是周末所以心里知道是等不来他们电话的。谁知妈妈竟然给小叔打来了电话,寒暄一阵后就让我接听。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不是下班的点,于是就问她,今天不上班吗?
妈妈支吾一阵后才说出了爸爸生病的消息。我了解妈妈,如果只是感冒这种小毛病,她是不会旷工不上班的。
到达后见爸爸的第一面是在医院里,病床都满员了,他躺在走廊的临时床位。在这之前妈妈带着他辗转到过两家医院,都没有床位,而病情也远远没有妈妈向我描述的那样轻描淡写。爸爸小时候肠胃一直不好,做过手术,至今在腹部留下了很深很长的一道疤。这次腹部疼痛难耐,在之前的两家医院输液很多次,都没有明显好转,也没有查出真正病源。
在等待医院空出床位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等待检查结果,检查并没有什么异象,只说消炎稳定病情后基本就没什么大碍了。于是又整天整天输液,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
爸爸明显憔悴了很多,他本就瘦小,现在更是皮包骨头。我性格随他,大多时候沉默寡言,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又无可奈何,甚至说不出宽心的话。只是在他想活动的时候拿着输液瓶,在需要的时候叫来医生护士,大多时候帮不上什么忙。他虽患病,但看得出他对我并不顺心。好在有我妈陪着他,总是在他还未说出口只一个眼神时就懂他需要什么,然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等来了床位,也等来了检查结果,需要做手术。直到此时我妈才瞒不住故乡的亲人们,毕竟爷爷刚离世不久,这笔不高的手术费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天价。妈妈是那种一贯不会欠别人东西的人,熬到这一步,也只得先求助兄弟姐妹们。
好在爸爸兄弟姐妹多,这笔钱顺利凑到,也终于要开始手术。
手术那天,从老家赶来送钱的叔叔、妈妈和我都在手术室外等着。
手术开始前医生告诉我们,这只是个小手术,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好了,接着给爸爸做了全身麻醉,推进了手术室。
三个小时艰难地熬过去,爸爸还没有出来,妈妈坐不住了,手术还没结束,外面不知道里面的消息,心乱如麻。五个多小时后,终于通知手术结束,医生拿着用塑料袋装着的一袋东西给我们看,那是爸爸被切除的肠。
爸爸的情况比想象中严重,整个肠道腹腔几乎全部粘连,倒进了整整三瓶药水才分离开,而切除的这一部分全都已坏死,足足有七、八十厘米,所幸手术还算顺利。
再在病房见到爸爸时,他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小时候手术留下的疤痕被再次切开再缝合,变得更大了,如那段被切除的部分一般大小。
麻醉剂的药效过去后,爸爸醒来,虚弱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不怕,我还有女儿。
嗯。我抓紧他的手拼命点头回答,一回头看到妈妈眼里闪光的痕迹。
那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爸爸最柔弱的时候,也是妈妈最坚强的时候,快二十年的分离让我们都不善于对彼此表达,却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彼此最信任的支撑,也成为我们之间最柔软的牵连。
手术后每天需要拔下身上那些管子消毒后再装回去。爸爸很怕疼,那也是他疼得最多的时候。我和妈妈像安慰小孩子一样哄着他,谁会想到那个抡着几十公斤大铁锤牛一样的男人,躺在病床上会像一只猫呢!
而爸爸也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铁匠,在病床上的日子,他还时常和妈商议着打铁铺的生意。本就是不定时接单,现在病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接活儿,对铁匠来说很危险。因为工人们急着用铁具,当然会去找别的铁铺。爸爸此时已经是这片区小有名气的铁匠了,有单的时候别人大多都会想到他。他手艺又好,能根据不同工种做出最合适的铁具,方的,长的,细的,圆的,短的……全都不在话下,甚至能根据使用频率的高低来精确材料,又不时接下修补、电焊等工作,我的爸爸,简直就是个全能人才。
可这场病,成了眼下最大的危机。这个世界正飞快地向前走,没有人会因为任何原因停下来等你。但有时看着这个爸妈待了快二十年还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城市,却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又陌生,又隐隐生出自豪感。虽然这里的一切我们还无法完全融入,可是仍在全力参与呀。你看,如果没有爸爸的铁匠铺,工人们就无法修路盖楼,人们就无法安居出行。我们虽渺小,也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上做好一颗螺丝钉的责任。我的爸爸,我真为他骄傲。
时间在输液瓶的滴管中一点一滴过去了,终于摆脱了比较大块的管子,带着被钉子钉满的伤疤,爸爸开始回家休养。术后休养已比之前好受很多,只是每天去医院清洗伤口,直至拆除腹部的那些钉子。
爸爸已无限为铁铺发愁,他不开工,我们家就没有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我妈每天没日没夜地在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也只够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而我即将步入大二,光学费就是一笔庞大的费用。
无奈之下,只好请来远在老家的二伯先帮爸爸顶着铁铺。二伯生得高大,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一次二伯打了30多根铁棍,第二天起床时喊着浑身疼痛难忍,直问你爸怎么受得了的?
我突然想起刚入大学的那个假期,有次爸爸接了很大的一单,有300多根铁棍。接到这种单真是又喜又愁,没办法,只得拉起炉火冒着扰民的风险从下午一直做到凌晨一两点。期间爸爸没歇息超过一分钟,总算按时交了货。想来那样的辛苦爸爸都自己默默承受了,从没向我们抱怨过一句。
说来很感激附近的居民们,自从爸爸从事打铁后,每天敲敲打打成千上万次经常到深夜,没有人抱怨过他,对我们都很和善。这城中村住着很多外来打工的人,有很多还是我们的老乡。真好,他们过得清贫,至少也不孤单。
沿海的夏天酷热难耐,租住的5平方米小屋对于爸爸的伤口恢复非常不利,于是在狭小的房间里装上了空调。这一装我妈待不住没开空调的屋子了,真无法想象,在之前的快二十年里,从没有用过一天空调的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大一的暑假结束,我又坐上了回学校的大巴车。走时爸爸身上的钉子还未拆除,大伯也咬牙接着铁铺的活儿。回到学校后没几天,爸爸就来电话让我找找网上有没有卖打铁的那种机器,有了机器他就能轻松点,还直说二伯干不了打铁的活,只有他能干,这活儿太累,不是人人都受得住的。
我心疼他,知道他虽病着,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铁铺,比谁都着急。现在手术后不到一个月竟然又想开工。我当然拒绝不了他,买了打铁的机器确实能让他轻松一点,要不然,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刚刚切除了那么大一段器官的人,能够抡起大锤去干那么粗重的工作,我怕他抻破伤口,怕他吃不消,怕失去他。
机器很快就买了,虽然后面实践证明打铁机不如人手灵活,大多数时候还是需要人手打铁的。就这样,小小的铁铺,放了沉重的打铁机后更加狭小。说是铁铺,这里更像是杂物铺,车胎、锤子、打气筒、电焊机、机油……对了,给人理发也是在这里。
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抡了一天大锤的男人,顺手拿起剪子,就在铁匠炉子旁边给人剪起了头发……我至今想起那场景,还有点懵懵的穿越感。
今年暑假,我实习了两个月才回家,铁铺已经变成真正的杂货铺,爸爸更瘦弱了,力气却很大,工友们有时拿他的铁锤作势挥动几下,无一不说只有他才能拿得动这些铁锤。多年的打铁生涯给了他强健的体魄,一点也想不到,这是动过那么大手术的人。
趁着回校的前几天,我缠着让他教我骑电瓶车,平衡力不好的我学得很辛苦,他教得也很辛苦,因为要一直跟在我后面给我扶车,他跟了一段后终于跟不动了,而我也始终没学会。他骑着车披着月色载着我穿梭在城市的边缘,我把手扶到他的腰上,心里震惊爸爸比以前瘦弱太多,腰竟已比我还细了。
转眼大学生涯就要结束,作为家中的独女,我深知肩负的责任。课余时间用以前兼职的一点积蓄做起了微商。爸妈都不会上网,但也从哥哥姐姐们口中得知一些我在网络上发布的动态。
前几天妈妈让我在网上给爸爸挑件衣服。要打铁烧不坏的那种,她开玩笑说。选了几件让他挑,左挑右选拿不定主意,又说这些衣服真贵。我说,你先挑着嘛。
这是我应该给你买的,以后会给你买更好的。我心里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知道他如果听了一定会高兴,但我们从来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人,对他的心疼与爱,只深深地藏在心里吧。
我的爸爸,虽然怕疼,却挨过很多疼,遭过很多罪;虽然性子有点懒散,却天晴下雨没日没夜地干着最重的活儿,为全家撑起了一片天;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却咬牙坚持供我读完大学……
爸爸,你是最普通的爸爸,却是我的英雄。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内心深处的隐秘而伟大。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