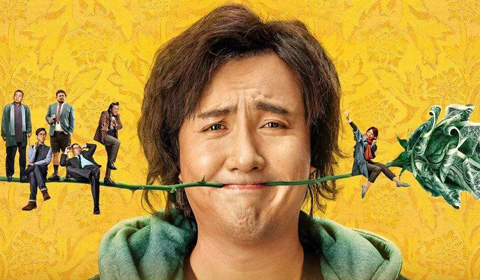亲情爱情:藏在枕边的爱
我的奶奶,享年92岁。
其实,直到奶奶离世后,她的出生时间仍是我们家族的讨论话题。对于这位一家之主,一位不认识字的老人,大家根本无从考究她的出生年份,她自己更不可能确切地记起。
奶奶的一生,姊妹缘薄,她是二姐,有几个兄弟姐妹。具体几个,我只知道一个巴掌数不完,妈妈曾向我清晰地数过,但我没有正确地理解。因为他们都在地球的另一边,每隔十几年,他们就分批回国,零零散散,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爸爸妈妈回忆说,奶奶不到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把她寄养在她的伯父家,卖了几头牛之后,拿着钱到了几千公里外的马来西亚生活,说日子富裕了就接奶奶过去。一晃眼,回来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奶奶嫁了人,已为人母。曾祖母给了她一笔钱,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座平房。此后,只有书信联系,奶奶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爸爸妈妈。
直到奶奶在生命的尾声,病卧在床,她的弟妹也未能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春节,在微信中视频,那时奶奶含泪看着电脑里模糊的妹妹,已经没有力气把声音传到地球的另一边。她渴望,渴望在自己最后时光里见到自己最亲的人。
后来我们总结,正因为奶奶兄弟姐妹缘份浅薄,所以特别疼爱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奶奶有句名言“年轻的需要自由,老的也需要自由”。我三岁时,爷爷就去世了,二十几年来,我们没有强迫奶奶跟我们到城里住,奶奶也从来都是在家里等我们回去看望她,回来,她高兴,没回来,她理解。
奶奶离世后,一幕幕美好的回忆不断浮现眼前,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她,也确确切切体会到,一个人活在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小时候,上幼儿园是我的噩梦,因为不喜欢群体生活,经常闹一些莫名的情绪,回忆起点点滴滴,都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患有自闭症。幼儿园就在我家隔壁,奶奶送我上学,去到门口才发现没有换鞋子,我猛地坐在门旁长条型蓝色的木椅上哭起来。奶奶赶紧跑着小碎步,再回来时已经拿着我的小运动鞋。这件事没有特别之处,但不知为何二十几年来我就那么清晰地记住了。
也许,是我不愿放下关于奶奶的一切。
上一年九月,弟弟上大学前,奶奶到城里住了几天,对我说了一件事。我有几个姐姐,当我出生时,爸爸问奶奶,又是女儿,还要不要。奶奶说她当时回答是,要!多辛苦都养大。因为奶奶的这句话,我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
前些日子,我突然想起奶奶,告诉男友这事,他说也许奶奶是把我当成了当年的她,她希望她爸爸当年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就不会让她近一个世纪孤身一人,我是奶奶平行空间里的另一个自己。我非常满意这样的分析。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我希望自己能活得像奶奶那样从容、开心,也感激她在我爸爸犹豫时给他指明方向。
奶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是含泪走过来的。春节前在医院,奶奶拉着我的手,问我今年过年想吃咸味粽还是芋头粽,我忘了我的回答,只记得脑子里全是泪。她坚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像从前那样照顾我们整个家族的每个家庭。
毕业后入职第一份工作,不错的单位。我告诉奶奶,我找到工作了。她躺在病床上笑着说,找到了就好,很好!翻开日记,回忆化成文字,不需费力,就能重新读一遍从前的自己。每次上学,奶奶都会给我一个红包,叮嘱我要快高长大,一直到大学毕业。“快高长大”一度令我温暖得整个人都要融化掉。我拒绝奶奶的红包,奶奶总会说,拿着吧,奶奶有can can(can can是奶奶自己发明对钱币的叫法),以后工作了攒钱了就给奶奶红包。结果,我第一个月的薪水还未领到,奶奶就不在了。
清理奶奶遗物时,我藏起了她生前常带的毛线帽。帽子里面有我认为珍贵的东西,奶奶的银发与茶籽油的味道,我看看摸摸闻闻,味道越来越淡,小心翼翼,担忧里面的银发会被风吹走,如同记忆般也需要好好保护。帽子上插着奶奶不久前亲手送我的银簪,那是她结婚时,她表姐送的礼物,花纹简约精细,人手打造,可好看。她那时就跟我说,她百年归老时,帮她好好保存。
我认同并喜欢这样一句话,作家林特特曾写到“写作源于总结癖,总结源于恐惧——人、事、风景,用笔记下仿佛就铁板钉钉,不会溜走,谁也抢不走。写作源于无能为力,试图用这种方式一再回到生命中难忘的现场,重温、反省、篡改结局。”
插着银簪的帽子,一直放在我的枕边,那是我对奶奶所有爱的封存,供我重温、反省,如果可以篡改结局的话,希望奶奶是位不老的人,我却是拼命长大的孩子。能报答奶奶,我不害怕老去,只怕爱的人等不到。
· 孤单的女孩有谁懂
· 什么是婚礼mv婚礼视频如何制作
· 自己如何制作简单婚礼开场视频
· 80后90后个性婚礼开场视频制作方法
· 我们谁也没相信 一定能在一起
· 那年友情:再转身已生死殊途
· 成长表白: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 青春成长:与坏孩子对峙的青春
· 史上编剧最好的绕口令配音员可以试试
· 周星驰电影剪辑结婚创意视频 星爷搞笑婚礼开场…
· 升学喜宴开场视频考大学搞笑开场预告片谢师宴金…
· 最新年会开场视频 搞笑年会视频 个性晚会暖场…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歌曲视频短片 晚会演唱…
· 年会歌曲串烧 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频短…
· 年会开场视频 年会励志歌曲 晚会正能量音乐 …
· 震撼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恢宏大气震撼晚会开场短…
· 搞笑年会开场视频制作 创意晚会暖场视屏短片 …
· 年会搞笑开场短片 晚会暖场视频 公司庆典创意…